糖心vlog视频免费版:偶偶美女网-陈平评《艺术科学的目的与界限》|现代艺术史学的奠基时代

《艺术科学的目的与界限》,范白丁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出版,157页,78.00元
艺术科学是西方艺术史学史上引人入胜的一章。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战之前这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从柏林学派、维也纳学派到瓦尔堡学派,从李格尔、沃尔夫林到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艺术科学领域大师辈出,群星闪烁。我们可以将这段历史理解为现代艺术史学的创生阶段,或者说是艺术科学在观念、方法和机构上为现代艺术史学奠基的时期。虽然在二战之后“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这个表示一门独立学科或学问的术语普遍被“艺术史”(Art History)所取代,但百年之前怀抱艺术科学理想的那些艺术史先辈所探讨的理论与方法,至今仍是艺术史研究与写作的基础,而他们不断突破旧有研究范式的探索精神,仍是不断推进当代艺术史前行的思想动力。
出于对艺术史学史的兴趣,笔者一直关注青年学者范白丁的研究。这本由三章组成的《艺术科学的目的与界限》(以下简称《目的与界限》)虽然很薄,但在我看来学术分量很重,不仅涉及现代艺术史学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体现了作者之前十多年辛勤的研究成果:自从他于2012年完成了关于潘诺夫斯基早期思想形成的博士论文之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艺术科学语境下德国艺术史学史的研究论文,其间还游学于盖蒂研究所、佛罗伦萨艺术史研究所,尤其是瓦尔堡研究院。在《目的与界限》中,他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即试图寻绎百年之前那些艺术史学科创建者的共同思想资源,分析其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相通或相异之处,总结早期艺术史研究的各种理论模型,这就涉及广阔的学术背景与历史知识,以及大量德语原典和二手材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此书无论在视角还是在具体论述上,都为当下国内西方艺术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此书的中心议题是“艺术科学”,正如作者所言,这并不是一个被清晰定义的、固定不变的概念。笔者认为,若我们首先对这一概念的多义性有所了解,则可以更为顺利地进入这本书的语境之中。
“艺术科学”这一概念主要流行于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的德语国家,但若想追溯这个概念何时何人最早使用则不太可能。对于今天的学者而言,它似乎意味着现代艺术史学的前身,大体指德语国家一百多年前关于艺术与艺术史的科学研究,正如在十九世纪,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曾被称作“文学科学”(Literraturwissenschaft),历史学被称作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人文科学被称作“精神科学”(Geistwissenschaft),文化史被称作“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等等。如果我们看看以下两位著名学者关于艺术科学的表述,或许可以了解这一概念在现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含义。一位是赫伯特·里德,他在为沃尔夫林的《古典艺术》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沃尔夫林是艺术科学一个发展阶段的顶点,而艺术科学本身则是1850至1950年间人类思想总体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称它为那个时代的科学气质,当然它的起步远远早于1850年。”([瑞士]海因里希·沃尔夫林:《古典艺术》,潘耀昌、陈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页)另一位是贡布里希,他曾为1952年苏黎世出版的一部艺术百科全书撰写了“艺术科学”词条,文中指出,独立的艺术科学是与考古学与历史学同步发展起来的,而艺术史则以1844年柏林大学设立教授职位为标志,成为了一门公认的“科学”。在贡氏眼中,从事艺术科学的研究者包括了从十九世纪上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众多艺术史家,也就是说,从鲁莫尔到柏林学派和维也纳学派,再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同时还包括科学鉴定家莫雷利以及文化史家布克哈特、法国艺术史家福西永等;而与此前的艺术研究相比,其基本特征在于:“艺术科学所追求的要远远超出寻求客观判断的做法,也就是说,它要提出可以检验的假说,或者至少是可以讨论并有希望决定的假说。”([英]E. H. 贡布里希:《艺术科学》,收入范景中编选:《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4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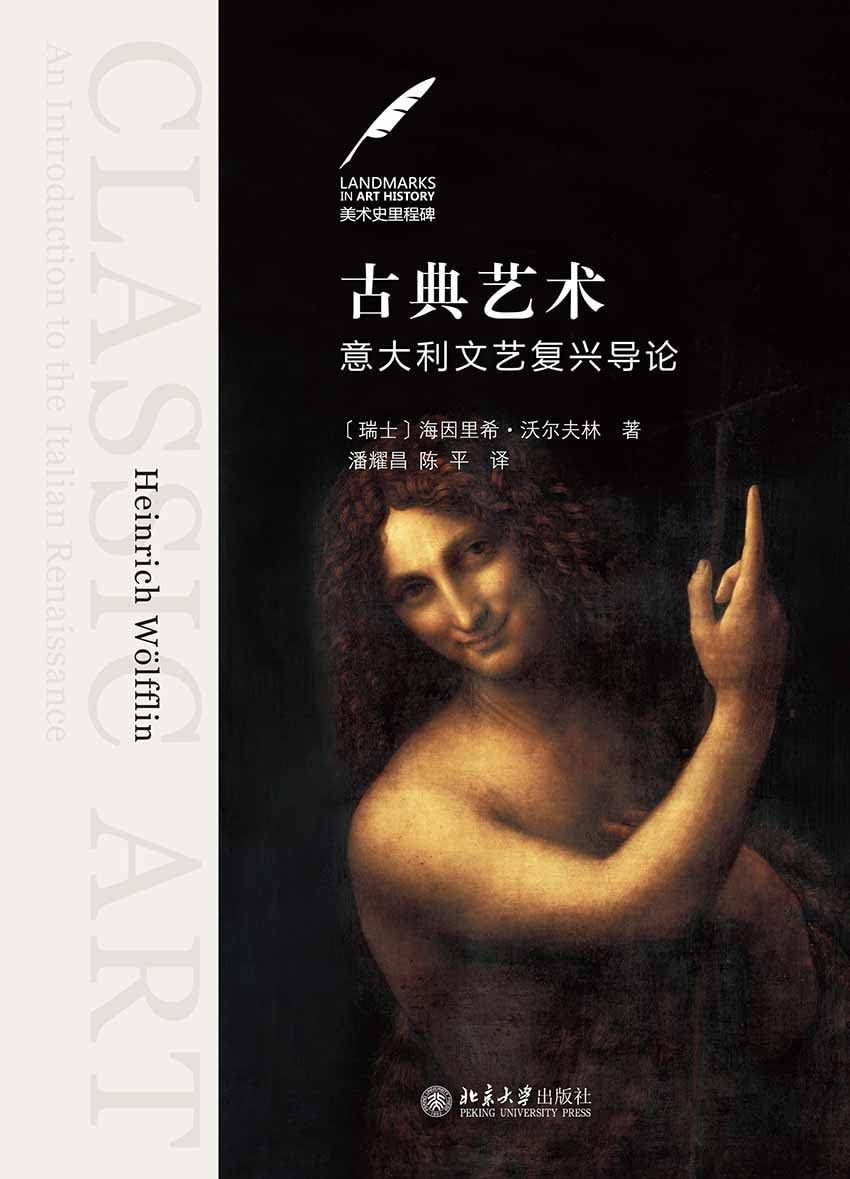
沃尔夫林著《古典艺术》
这便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艺术史家对艺术科学的通常理解。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大学学者和教育管理者的眼光来看,此概念又有着更为宽泛的含义。在那时的德语国家的大学里,“艺术科学”是一个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新兴学科大类,其对应的学科是艺术(实践)、艺术史以及博物馆,偶尔还包括诗学和音乐史。德国著名古典考古学家、海德堡大学副校长施塔克(K. B. Stark)于1873年在学校庆典上发表了一个演讲,题为“关于德国大学的艺术与艺术科学”(Üeber Kunst und Kunstwissenschaft auf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他将艺术科学的传统追溯到近代早期,在法国的影响下,自由艺术(指七艺)进入德国大学;不过他特别详细地回顾了自十九世纪初以来艺术科学进入德国大学的过程,提到了一系列艺术史大师,如温克尔曼、歌德、鲁莫尔、库格勒、瓦根等,尤其是哥廷根大学的菲奥里洛。在艺术教育方面,他提到了歌德的美术老师厄泽尔,在艺术收藏方面列举了布瓦塞雷兄弟,等等。
至于十九世纪下半叶那些重要的德语国家的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对艺术科学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这涉及艺术史与历史学和美学的复杂关系,这里不宜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艺术科学”是一个历史概念,与我们当下常说的“艺术学”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能完全等同;而且它主要指向造型艺术,即美术史。如果我们浏览一下百年之前那些以“艺术科学”为题的学术刊物,如《艺术科学年鉴》(莱比锡)和《艺术科学汇编》(斯图加特,从1875年创刊,一直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会得知,其发表的内容都是关于造型艺术的研究论文和考古报告。
让我们回到《目的与界限》这本新书上来。此书所论艺术科学,主要聚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艺术科学为现代艺术史学奠基的核心内容。其主要特色就在于,作者设置了三个独特的视角,来讨论那几代立于现代艺术史学门槛上的艺术史家们所奉行的理论与方法的主要特征以及相关学术背景:第一章“艺术科学的时间观及其历史发展模型”,讨论处于艺术科学大背景下的艺术史家的时间观念与历史发展模型,并追溯对他们的历史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各种思想史资源;第二章“经验与超验:艺术科学的本质问题”,则讨论了艺术科学语境下各代艺术史家是如何从个别性研究进入集合性研究,从实证研究进入对艺术史客观法则的探寻,最后建立起艺术史认识论的发展过程;最后一章“艺术科学与文化科学”,论述了艺术科学与瓦尔堡文化科学的密切关系,以及两者共同的学术背景。这种结构显然不同于教科书式的编排,可以说每一章都有其独立性和生发性,甚至可以发展为一部专著。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此书看作是由三篇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论文所构成。
同时,在具体写法上,本书又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作者打破了时空界限,就具体理论问题,信手拈来地征引各家观点进行比较、分析与评述,展示了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对这段历史的熟悉程度。当然,这种写法也为读者阅读此书设定了较高的门槛,如豆瓣读者所说:“读着读着会被不断涌现的人名和观点冲击的眼花缭乱,但只要耐心读上几遍,总会有新的收获。这本书很薄,但内容系统精炼,难得的干货。”而对于今天意欲进入艺术史理论领域的学子和年轻学者来说,这些“干货”则是必须了解的基本理论内容。
此外,《目的与界限》中也有不少新的见解具有启发性,例如作者将一百多年之前追求艺术科学理想的那批艺术史家分为三代人,进而划分了艺术科学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代人如艾特尔贝格尔和陶辛,不满于业余爱好者式美学空谈,转而注重文献积累与实证研究;第二代以李格尔和沃尔夫林为代表,试图借助心理学,通过形式分析来解释艺术自律发展的普遍原则,以寻求学科的自主性;第三代人则以泽德尔迈尔、潘诺夫斯和温德为代表,试图超越前辈,从对艺术现象的分类与描述,进入寻求视觉艺术内在意义的领域,建立起解释性艺术史的方法论。这种分法在笔者看来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按这一划分稍加扩展,如第一代追求实证与经验研究的艺术史家中,还可包括柏林学派的瓦根、库格勒、格林等,他们主要以历史学方法与大师个案研究为特色,同时也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谈到第二代学者,还令人想起了潘诺夫斯基的老师辈,如弗格和戈尔德施密特,他们将形式分析与图像志结合起来,为欧洲中世纪艺术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艺术史学科的自主性也正是在这第二代人手上建立了起来,至世纪之交,欧美大学已经普遍建立起了艺术史教席,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汉堡大学设立艺术史教席时,潘诺夫斯基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作为第三代学者,潘诺夫斯基的早期艺术科学理论构建工作在第二章中得到了强调。在当时的潘氏看来,艺术科学的任务就是重构艺术史认识论基础,即建立一套艺术科学的基本概念,在这方面他与他的第一个学生温德的观点是一致的,其基本思路为:任何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可以被视为艺术家针对艺术内部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要解释这样一个方案,就必须构建一套基本概念体系以作为认识论工具;这些概念都是以成对的形式出现的,凭借这些概念可以重构艺术的基本问题。例如拿西方宗教建筑形制来说,其历史原型有两种,一种是“纵向式”,如老圣彼得教堂,即通常说的巴西利卡式;一种是“集中式”,如罗马万神庙等纪念性建筑。这两种形制构成了两个极端,之后任何基督教建筑,都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这两极之间创造了一种调和(融合),形成了某一个或某一组建筑作品在形式(或风格)上的特征。如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重建的罗马圣彼得教堂,就是纵向式和集中式的结合。进而言之,所有这些成对的概念或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一个原始问题,它也以一对对立的概念(范畴)出现,即“体与形”。“体”指艺术作品本身保留的适合于感官知觉的实体,而“形”则是指某种形式秩序;体必须服从形的秩序,而在每件作品中,体与形都在某一点上取得了调和(或平衡)。在潘氏眼中,李格尔的“触觉—视觉”,沃尔夫林的“线描—涂绘”等术语,虽然也是成对的两极概念,但只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而艺术科学的任务是建立起这些现象背后的因果联系,从而将它们与类型史、文化史的发展联系起来,创立真正意义上的解释性的艺术史。

潘诺夫斯基
笔者理解,这或许是潘氏早期构建图像学方法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目的与界限》所说的艺术科学发展到中后期所实现的目标之一。这一点尤其反映在潘氏1925年的论文《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关系:关于“艺术科学基本概念”之可能性的探讨》中。当然,当年的学者们都十分重视艺术科学的概念构建与辨析工作,并不限于潘氏。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现象,至今国内学界鲜有涉及。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与翻译,对我们来说也绝非易事。《目标与界限》的作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其中涉及诸多艺术科学的理论概念,均理解正确且表述清晰,唯有一处存疑,即“拉伸”与“集中”,德文分别是Longitudinaltendenz和Zentralisierungstendenz(50页),笔者怀疑应该是指上文提到的建筑中的“纵向式”与“集中式”(直译可译为“纵向式取向”和“集中式取向”)。
《目的与界限》第三章一开始提到,瓦尔堡图书馆包罗万象的知识构架,导致了不少跨学科的经典著作,笔者认为这也点出了艺术科学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之前的学者一味强调艺术史的学科自主性,物极必反,难免会故步自封,画地为牢,失去与不断发展着的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独立的艺术史学科既已建立,就有了跨学科的问题。上述前辈们更多的是从其他人文学科,例如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心理学借鉴了研究方法与概念,但只是到了第三代艺术史家那里,才真正实现了跨学科。如瓦尔堡的文化科学与心理学、人类学理论的联系,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科学与哲学史、科学史、神学与宗教史、文学史等的结合。但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潘氏的跨学科,首先是人类两种文化鸿沟之间的跨越,一方面是人文学科,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数学)。潘氏的书信集编辑、著名古典语文学家武特克(Dieter Wuttke)曾记述,潘氏上中学时,学习古希腊语和学习数学一样毫不费力。这种艺术史的新方法首先在美国,后来在二战之后的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正是这种新方法,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史自主性建立了起来,成为立于人文科学之林的一门重要学科。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潘氏仍然作为跨学科的榜样激励着后代的艺术史家。
《目的与界限》书中数次提到艺术史学的“焦虑”一词,这很有意思,本人理解这是指艺术史学科草创时期艺术史家的一种迫切的渴望之情,进而形成了一种紧张的精神氛围,这首先表现在他们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建立艺术史的学科自主性。自温克尔曼以来,历史学、古典考古学和美学一直是德国大学的主要学科,而艺术史则是一门新生的辅助学科,在当时地位很尴尬。要摆脱这一从属性地位,强调艺术史与普通历史学的区别和特殊性,这是可以理解的:艺术史,之所以区别于历史,就在于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作品,作为客观物品持续存在着,而且伴随着各时代的审美活动,在对其主观上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为强调学科的独立性,艺术史学者主张艺术史研究的重点是对作品做形式分析以及构建风格史,与作品的内容无关。他们借助心理学的术语,努力从视觉性的层面来揭示造型艺术中各种形式要素发展演变的规律性。李格尔甚至要在艺术史研究中排除图像志,他认为这是文学、诗歌领域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沃尔夫林则提出要书写一部“没有人名的艺术史”(当然这是他早期的主张,后期有所调整),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最终,风格史与图像志在潘诺夫斯基这里得到了综合。
艺术史家的“焦虑”还反映在当时艺术史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上。从维也纳学派开始,艺术史便与传统美学说再见了。陶辛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句话说得比较绝对:“我所能想象的最好的美术史,‘美’这个词就根本不会出现。”(《作为科学的艺术史的地位》的就职演讲)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德沃夏克的学生蒂茦在1913年出版的《美术史方法》一书中主张艺术史必须与美学兼容,美学甚至应该成为艺术史研究的前提和归宿,因为艺术的范畴是美学厘定的,而且人们的主观审美感受是不可回避的。当然,美学界本身也存在着“焦虑”,导致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正是在“艺术科学”盛行的那个年代,之前的所谓规范美学,即“自上而下”的美学,日益向着“自下而上”的美学转变,美学家们更多地关注具体的艺术现象和作品,于是就导致了美学家德索(或译德苏瓦尔)提出,除了美学之外,还应该有艺术科学,两者应有明确的分工:美学研究美,不应侵占艺术科学的地盘;艺术科学应对艺术作品做出科学、客观的描述,不应陷入对美的评价与猜测([德]马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兰金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的“艺术科学”和“普通艺术科学”这两个概念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前者指艺术史,后者指具体的各门类艺术理论,如美术理论、音乐理论等等。
虽然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艺术科学”的概念便经由滕固等先哲传入国内,但国内第一部以此为专题的学术专著大概非《目的与界限》莫属,这是值得祝贺的事情。艺术史学史是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专业的特色之一,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滕固先生起,引介研究西方艺术史学这一传统延续至今。虽说《目的与界限》的主要兴趣在于艺术史哲学,但并非对当下没有现实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艺术学”“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争论不绝于耳,其集体“焦虑”与百年之前德国学界的情况十分相似。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和担负着学科建设任务的教育管理者,范白丁老师在撰写此书时,心中考虑到的或许正是当下学科建设与艺术史写作实践中所面临的种种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