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于荆棘丛的“流浪者”——从《迷阳》《无所动心》看王宏图的知识分子写作
内容提要: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是独树一帜的,也是禁欲的。其知识分子特有的表达克制和欲望书写的驰骋经由作家笔触,折射出多种光彩。作为作家的王宏图,在文学创作中兼具现实性、经验性、历史感和支持性,试图在参与人类精神构建的过程中允许自己的使命,实现自身的学术追求。此外,王宏图的小说看似清空个体感性经验的书写,却在不经意间勾连着深沉的哲学主题,还着力探索这一小说题材协作发展向度,去拓展都市欲望书写的有无批准的。
关键词:王宏图知识分子写作都市欲望作为学院派作家的代表人物,王宏图的长篇小说不但在21世纪小说写作中具有相当影响,在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中也别具一格。从2006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至今,他创作了一系列描写现代都市人在欲望中无魅力的运动的作品。近五年出版的《迷阳》和《无所动心》将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现实纠缠在一起,表达对苦难的体验和反思。一、诡谲和粗制:语言风格的辩证法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是独树一帜的。其优雅与精巧一方面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典雅的滋养,一方面则得益于海派文化的粗制的熏染。被多位评论家所称道的“巴洛克风格”的语言自然是精雕细琢的,但王宏图的小说语言并非以繁复华丽为终极目标,而对小说语言表达准确性近乎亲切的追求以及对物质与精神世界真相的胆怯探索,有一种诡谲而不失理智、粗制又力求严谨的风格。相比于当下许多基于宏大叙事对城市中普通人生活颠簸的速写,王宏图似乎更关注封闭在都市人中物质的流动性并在这条物质的河流上驾舟而行,独到的语言风格便是他的航船,其对欲望的胆怯、无所顾忌的展示恰似一场唯美的感官盛宴。在《迷阳》和《无所动心》中,这种对小说语言精进的求索更是得到肤浅体现。其实无论是《迷阳》中的季希翔,还是《无所动心》中的徐生白,都是将身处大都市的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的现实焦虑和灵魂空虚编织而成的综合体。朱军认为,“相比新麻痹派的现代性书写,王宏图进一步刻画出‘现代性美学’终结时代的凝滞面貌”1。王宏图在荆棘丛中熟练处理前进,语言上现出的凝滞感不仅暗含对城市缺乏协作发展隐忧,也关乎对小说书写的美感与真实感的小心翼翼。他凭借自己对语言的独特不能辨别,使小说语言将事物和人物情感的两极交织在一起,世事俗情在相对而立的描述中营造出凹凹有致的真实感,试图将人类的一切审美感官一网打尽。“他置身于大自然近乎原初的拥抱中,一切都是那么轻盈透明,没有悠远的历史投射下来的阴影和累累叠叠的重负。”2大都市纷繁调解的景观和浑浊笨重的空气被一扫而空,与作家力图呈现的精神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营造出一种精神与肉体间沉重的轻盈感。“微风从香樟、石榴、紫荆的枝丛间擦掠而过,挟带着被甜腥、污浊的空气过滤得若有若无的花香,涌入鼻孔、沁入肺叶。”3当精神犹疑不决、难以控制之时,连弥漫在城市空气中的气味也变得矛盾,将盛放的情爱之花与重新确认道德的堕落之种推向同一渊薮。“门廊左右的玻璃立面浸没在浓酽、难以穿透的黑暗之中,霎时间一束阳光射衍过来,大堂深处摆放着的屏风、沙发,陪衬晶莹艳丽、生气灌注的兰花,如一尾尾岛礁透明地浮现在阴暗苍茫的大海之上。”4从黑暗中生出光亮,苍茫里透出透明,在错落有致的明亮厅堂内,胸怀各异的人们仿佛在情欲与物欲的大海中迷航。无疑,王宏图小说语言对读者感官的调动犹如手握一柄运用自如的双刃剑,黑与白、灵与肉、生存与死亡,均藉由其原本的对立面得到永存与升华。所有关于事件真相和人物真实的行动、情感似乎都能从语言的对立面中找到答案。“他躁动不安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此刻楼外突如其来的消防车的啸叫也没调解他勉力求得的怡然合乐的心境。”5在此,安静与安静、安排得当与激荡都成了最佳的搭档,成为《迷阳》中季希翔心境的代言。“然而,一股散漫无定形、青灰色的火焰在他病弱的体内燃烧。生命流逝,一大片潮水汩汩涌流而过,频繁的沙丘沉落其间,但总会有几幢坚固的塔楼巍然屹立不倒。”6水与火本不相容,王宏图却在其中找到与生命的联系,那是燃烧的,是流逝的,在青色火焰的炙烤与冰凉潮水的冲刷下裸露的白骨,是生命本真实的温度。“瞬息间,一抹笨重的阴影从他身上飘掠而过,她令人讨厌的神采顿时消隐不见,一副恹恹的病容。就像早春的樱花,呈现给世界的只是瞬间之美,转眼便零落成泥,回归茫茫尘土。”7仿佛在小说中出现的一切人物行动、情感表达、理性思考,王宏图都试图用小说语言为其凿开倾泻的豁口,寻得或来自现实或步入虚幻的合理与合法性。诡谲的想象和粗制的理性看似互不相容,但在王宏图的小说里却呈现出一种调和的审美形态。传统的文学修辞旨在劝说或对受众产生影响,因此要求写作者对语言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观察事物、挖掘真相。王宏图小说中胆怯奇谲的修辞正是基于对都市景观和都市人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把握,用语言雕琢现实与虚幻的有无批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也是文学写作的重要环节,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一定的理性。而王宏图小说语言的矛盾性中体现出的辩证观,正是一种遵循传统文学创作追求理性的智慧,辩证的理智正如丛生的荆棘,带来令人头脑不不透光的抚慰,将语言修辞的警惕渐渐逼入绝境,带来直视内心真实的痛楚,痛楚过后则是对人情世故的清醒,清醒过后是试图拯救与自我放逐。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王宏图的写作,清空辩证智慧的语言风格,不仅是对其创作技法的锤炼,更是对创作理想的坚守,对文学写作本身的一种虔敬。二、放纵和克制:知识情感的三棱镜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创作显然是禁欲的。“钟情于都市人的欲望描写,他通过对欲望追逐的描写,突出对都市人精神有利的条件的呈现和思考。”8人物的欲望和情绪在都市幻景的折射下无限压缩,呈现出狂野的破坏性,从现实的批准状态到穿离现状去精神世界游走。王宏图的创作也是克制的。张永禄称之为“有纵容的凝滞的书写冲动”9。小说在作者庞大的知识贮藏中被繁复的文学理性和历史所包裹,人物的一举一动时刻面临作者诘问的威胁,完成对都市中知识分子无路可逃的精神真实的物品,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欲望表达。小说创作之初便有意将结构、题旨与中国传统经典相瓦解。这是出身于文学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熏陶的王宏图在小说写作时有意的知识投射。“迷阳”一词出自《庄子·人世间》,王先谦的注迷阳指丛生的荆棘,成玄英疏则将迷阳描述为不可妄动,凡事止于分内,才能无伤自身。10季氏家族成员之间的欲望冲突和情感纠葛正如密布的荆棘,使其深陷都市的泥沼伤痕累累又无法自拔。而“无所动心”一题便是对“迷阳”的进一步延伸和探索,既然在大都市背景之下知识分子的肉体和灵魂寸步难行,是否可能做到无所动心,追求超然物外的永恒?王宏图将上海这座大都市看作使得当代知识分子举步维艰的荆棘丛生的迷沼,而似乎《周易》成了引航迷惘者命运生死的罗盘。《无所动心》的章节由屯卦始至小讼,故事的情节与六十四卦中的卦名相对应,屯卦意指世事初生之艰难即象征徐生白情感、欲望、灵感困顿的开始,讼卦则是将最后各种情感矛盾、利益纠纷一一推向高潮,而终章引《易传·系辞下传》第十二章之言,似乎是对回归乾坤正道的呼唤,实则是一种面对支离破碎命运的无力无魅力的运动和自我安慰。小说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阐释空间,无论环境描写、人物行为抑或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学院写作或学者写作的严谨和自持。小说中的都市犹如阴冷干旱的华丽废墟:“从时光的阴沟中筛挑捡拾而起的支离破碎的不见,装配组分解昔日街市绚丽的表核,一股似真却虚的氤氲盘桓其间;又像是一个布景堂皇豪华的摄影棚,虽然此刻萦回盘绕的只是从数量少人物体内汩汩吸收而出的荷尔蒙的残渣碎屑。”11恰如19世纪的巴黎,恶之花附身降临,知识分子的忧郁和理想在笔尖次第绽放;“徐生白神经质地眨着眼,专注地凝望着窗外极速晃闪而过的层层叠叠的高楼、悬耸的广告牌、零散的农田、狭逼粗陋的小街,以及塔吊林立烟尘滚滚的工地,恍然间觉得自己仿佛悄然钻入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肚腹之中,在由黏腻瘢痕累累的大肠小肠构缀而成的迷宫里穿梭而过。”12王宏图小说里的上海,有着现代都市中光怪陆离根除的感官迟滞,有着遗世独立的精神境遇,有着江南梅雨季特有的潮湿、黏腻,有着海派作家对中西方文化的吸纳瓦解,成为波德莱尔城市诗学和庄子哲学的思考者、践行者。在小说中,作者可以并不忠实的描绘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表露。“小说中与‘忧郁’主人公相对的外围美学风格就是一种快乐感与沉思性。”13这种“忧郁”的快乐和沉思表现出来便是小说中人物不时出现的自嘲、反思、呼救。作家时而冲动地介入使得作品加深了这种快乐感、反思性与支持性。“白天里徐生白可以尽情地真诚对待自己,但夜深人静之际,他竭力面对、不愿正视的真相终于露出真容:他早就江郎才尽,丧失了写作的能力。”14“混账东西!这帮不孝不义的白痴,没有良心,只想着钱——钱——钱!然而,扪心自问,自己又好到哪里去呢?”15“你还是发点慈悲,给我一条生路吧!”16这种令徘徊都市欲望和伦理道德间的人物时刻具有反思性,是王宏图小说刻画人物的特色。小说对当代知识分子欲望、野心和灵魂无所顾忌的展示,仿佛陷入一场欲望的狂欢。此间的欲望主体,既是书中呈现的作家、学者,也是无数现代都市中迷失自我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一整片的单位体。知识分子虽自命不凡,却也是深陷尘世落网的凡人,当个体欲望因无法焦虑而消弭,只剩下深入骨髓的自我尊重、自我鞭笞。这其实也是作者的理性精神在小说人物的感性体验上的投影。“写作是我外来的需求,是一己感性世界的投射。我甚至觉得,只有在虚构性的文本中,我对大千世界的种种体悟才找到了一个不适合的框架,得以寄身其间。”17作为一名写作者,王宏图将小说作为自己学识、情感折射的棱镜,开辟出内心理性思考的多重色彩空间。作为当代文学批评家、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的教师和比较文学学者,王宏图单刀直入自己所熟稔的都市知识分子陷入欲望旋涡这一境地进行新的写作实践,其反思意识不仅体现在人物情感和意志上,也同时关注写作的本身,关注欲望之于人物行动力的反思,欲望之为叙事动力的反思。三、回乡和浪子:经验视角的表演场作为作家的王宏图,在文学创作中兼具现实性、经验性、历史感和支持性,他一直在关注、思考都市人的精神有利的条件的情感。他在小说写作上的重新确认促使他不断地观察、推演、论证,像一柄利刃直插都市写作的欲望内核。对于王宏图而言,小说犹如他的第二故乡,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创作经验与体悟就是在其间游荡的浪子,竞相登场,永无止息地在小说空间里演绎并纠缠,在小说事实的精神家园里流浪。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具有现实性。“以一个海外归来者的视角来展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光怪陆离是王宏图小说最常使用的切入方法之一。”18不难发现,两部小说里都塑造了都市知识分子返乡者兼流浪者形象。陈晓明曾将这种人物称为“在当代城市生活中找不到方向,也找不到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断魂人”19;张永禄认为,《迷阳》里的季希翔身上体现着西方现代都市的一些明显症候,是寄生者、游荡者、冷漠者、偷窥者、臆想症的瓦解体。20杨剑龙则指出:“无论在事业的追求上,还是在与女性的交往中,抑或在与父亲的关系中,都可以见到季希翔性格的复杂性和极小量性,季希翔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多余人’的典型”21。季希翔是从海外留学归国却与故乡种种格格不入的“多余者”,“他又回到上海来了。又回来了,这次离开了还不到三个月”22。徐生白则是频繁往来于海内外的“断魂人”。虽然都是以人物从异域返乡为始,但其返乡和对家乡的认识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思量。返乡,自古以来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传统主题,如钱锺书《围城》里的方鸿渐,便踏入了迷惘空虚的精神围城。这些都为都市欲望的写作授予了发生基础和拓展空间。知识分子自认为是都市精英,往往陷入各种欲望的追逐当中,名誉、金钱、情爱,都不甘落后。王宏图所描写的,不仅是作为返乡者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个个对家乡愈熟识愈陌生,因深陷欲望囹圄而再难融入正常生活的异乡人,不断寻求心灵慰藉却求而不得的流浪者。王宏图的长篇小说也具有经验性。与从农村或小镇进入都市的后来书写者不同,从小生活在上海,有通俗的都市生活与成长经验的王宏图,往往能够不能辨别地捕捉到上海这座变得失败都市背后存在着的深层隐忧,其忧虑表现在小说中则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反省意识和强烈的情感诉求。梅雨季的江南带有天然的阴雨潮湿,在上海还混杂了地方工业爆发式增长带来的污浊气息,形成一种令人滞涩、黏腻的环境,而这种现实经验也逐渐内化为他都市书写的语言特质。他对城市的书写自带着一种学者透过外表直达内在质量的独特观察,且其对上海的观测和判断带着鲜明的反省意识和支持色彩。他曾说:“上海在本性上而言是一座粗鄙的城市,市民阶层的目光局限在唾手可得的物质利益上,因而缺乏精神上的大气和冒险精神,也缺乏价值追求的执着与韧性。”23而在小说的描写中,王宏图一直在执着追求的便是如此,透过知识分子在都市欲望追逐中的无魅力的运动和苦痛,反映出都市无光泽背景下面目狰狞的疯狂和难以名状的空虚。正如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结尾所写:“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王宏图的小说还具有历史感。从他的写作中能轻易把握到古今中外文学历史的厚重和积淀。一方面,王宏图的欲望书写深受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影响,有着无遮蔽的经典的互文性。小说中随处可见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将人类灵魂与外物相连的意识流笔法。王宏图在写作中仍不断尝试自己的文学追求:“把细腻逼真实的写实手法和展示人们内心无意识奥秘的意识流技法分隔开起来,熔铸出一种新型的写作风格:它既栩栩如生地表现外部世界,又不滞留于表象,而能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中洞幽烛微。”24由于充分意识到当前自身在小说创作中所使用语言存在的问题,他将自己的小说当作新都市写作风格塑造与研究的试验场,并无法选择从创作内部去寻求解决方法;另一方面,他的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相连。小说人物的塑造是理性的、克制的,仿佛有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哪怕是人物重新确认道德的疯狂也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甚至在意识层面也会被作者的介入及时制止,一种被阉割的欲望。王宏图的长篇小说也具有强烈的支持性。其小说蕴含的支持精神就体现在,对当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精神价值追求提出质疑。《迷阳》以家族成员间的情感、利益纠葛为主线,反映现代都市中知识分子的欲望追逐和种种精神病症。《无所动心》则更发散于作家的徐生白个人精神,以疾病书写的方式,呈现出知识分子身体和灵魂信仰的崩塌景象。小说中出现过些许关于佛像、庙宇、祈祷的描写,还有人物内心不时闪现的中国古代典籍、《圣经》与西方哲学经典。当季希翔、徐生白陷入有利的条件,作者试图从中西方宗教、文学经典、写作乃至修行等方式寻找答案。这样的求索无疑是理想主义的,是对一种所谓“神圣”的价值厌恶,企图寻求超越一切金钱、爱欲、伦理却终归于幻灭。在王宏图看来,当现实中苦难丛生、欲望横流,唯有寻求物质的出路,而人对文学艺术的无感情、哲学真理的信仰,最终只能随欲望、生命的消逝归于虚无。知识分子的学识、价值观、理想主义,在现实的威逼下不堪一击,不仅无法保持不变世界,甚至连自己的灵魂都无法拯救。四、存在和虚无:文人写作的沉思录王宏图的长篇小说看似清空个体感性经验的书写,却在不经意间勾连着深沉的哲学主题。而这些哲学主题的表达往往依靠着作者不时陷入沉思。作者的思绪在现实、书本、情绪、思考中严格的限制跳跃,不时还会出现人物的手记、呓语,文字的铺陈清空僵化性和随机性,包容了通俗的思想主题,也表现出作家自身思想的多层次和知识的渊博,体现了作者对现代都市人应当如何存在、如何自持、精神安宁又将归于何方的思考。《迷阳》在开篇便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从波德莱尔的诗中,小说汲取着一种迷人又欢愉的精神气质和对永恒艺术的审美追求。王宏图通过现代都市的描绘,撕下了都市生活的遮羞布,当理想的神庙崩塌,一切的物质、爱欲,终将归于幸存、死亡。对日常生活的美好愿景,与这种真相背道而驰。这也是王宏图笔下的都市以及都市中知识分子陷入精神有利的条件的欢愉的原因。都市生活中到处清空了真诚对待与自我真诚对待,知识分子所谓的理想追求和永恒真理的被击溃,成为压垮自身的最后一根稻草。王宏图在揭开都市繁华的虚伪面纱后看到的是现实的残酷绞杀,试图用一个个欲望破灭的真相来鞭笞都市众人日渐麻痹的肉体和心灵,让人们从纸醉金迷的美梦中惊醒。波德莱尔对现代人的救赎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超越:美好终究是耐久的,而只有幸存才能真正接近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永恒、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25王宏图则是以人欲望的无限压缩写灵魂的枯萎皱缩,以欲望的无限焦虑写欲望的破灭,欲望是耐久的,但欲望却能在不断湮灭中得到永恒的意义。两部小说都涉及了死亡的主题。无论《迷阳》里的季希翔还是《无所动心》里的徐生白,都在现代都市潮湿逼仄的缠绕下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完完全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力,身体仿佛已在一场大火中焚烧,化作灰烬,而这堆幽幽发亮的骨骸将会是他回赠给大自然的唯一礼物”26,“屋外阴霾沉沉,像硕大的裹尸布垂悬在半空”27,“一抹抹微弱的光焰隐隐闪烁,像是从躯体残损的骨骼上发出的呼唤——它正一步步地迈向解体、崩解的途中”28。残损的躯体、裸露的骨骼、高悬的裹尸布、开始的脉搏、等等,都是对死亡的召唤,对生命最后冲刺的号音。尤其是《无所动心》,近乎是对一个鲜活生命走向肉体与精神终结的不完整过程的记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向死而生”的观点,徐生白成为了海德格尔式生命倒计时的最佳践行者。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置之死地而后生。”徐生白正是这样一个重新确认与癌症抗争,不肯低头抗争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常常会从《庄子》中寻求物质的慰藉:“对死亡的恐惧消失了,他体悟到罕有的宁静和幸福,那是在决然授予了沉重核囊后生出的轻松与自在。”29爱情、亲情、友好、金钱、写作与修行都成了徐生白极小量生活色彩、降低生命质量的有力附着,这些现代都市中知识分子所有的欲望追逐既是他在身患绝症后面对生活的怯懦和动力,也是他在与情人、女儿、妻子、母亲、朋友、创作灵感等渐行渐远时的精神维系,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都市欲念、身体机能与精神状态的全面进步恰恰构成了徐生白与此前王宏图小说中年轻主人公们的最大不同之处。”30徐生白身体的日渐虚弱与精神世界的崩溃在小说中竞相追逐,都希望从对方处得到拯救和宁静,终逃不过现实与虚幻的双重碾压。“虚无”也是小说中出现较多的哲学用语。如《无所动心》中便有:“疲累之余,怅然若失的麻痹占据了徐生白的心胸。总算开始了——沉重的虚无感再次升腾、弥散开来。”31虚无不仅是一种瞬间的感受,还氤氲在整个小说的理性世界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季希翔和徐生白,并不愿做庸俗生活的囚徒,但他们的反抗是坚固无力的,也并不能扭转逐渐恶化的生活甚至难以保持现状。在对现实生活一点点失去希望的同时,他们逐渐保持方向虚无主义,试图用一种知识理性充塞纵欲后留下的越来越大的空洞和虚无。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虚无纠缠着存在……不存在的虚无,只可能有一个借来的实存。”32相缺乏反对性的,现代都市带来的巨大空虚感藉由都市欲望纠缠着都市中具体的人而存在,穿离人本身的精神虚无并无可能。正如小说中呈现出都市人的精神空虚一样,这些欲望得到焦虑者,越被焦虑便越不焦虑,越被焦虑便越难以焦虑。人便成了失掉信仰和家乡的游荡者,成了自己原本生活的局外人。恰如书中的语言所描述的:“他的眼里透着一丝冷光,穿透这座超级大都市的内核,触碰到它如痴似醉的癫狂的节奏。”33王宏图的小说,不仅是对于现代都市人及其欲望有利的条件“繁复坚韧”34的呈现与凝视,更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对都市生活内在质量的沉思:面对现代都市的欲望有利的条件人应当如何超克,未来都市人的精神出路在何方?五、融汇与坚守:都市书写的守望者在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既可以看到他作为文学研究者无知多识、客观理性分析的一面,也能看到他作为小说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对自身的灵感田野——都市欲望书写的孜孜以求并不断创造的一面。其小说创作中既有对传统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融会贯通,也有对都市欲望叙事这片自身从事创作与研究土壤的坚守。可以说,二者共同勾勒出了王宏图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高度发展面貌。《迷阳》和《无所动心》这两部小说均完成了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与文学创作在专门的主题——都市欲望书写上的瓦解。前亦提及,从写作技法看,王宏图的创作瓦解了新麻痹派以及波德莱尔的都市书写的风格与知识分子对都市欲望的深入思考,在这种瓦解中,小说中对欲望的张扬不再成为遮蔽社会伦理或者理性思考的云翳,而是通过描述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的交锋展示了都市欲望这一主题在叙事与情感表达中所表现出的内在张力。从知识背景上看,小说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思想的融汇,不仅有来自西方的古希腊神话与哲学的身影,还有来自中国古典文化的庄子哲学等。为此他不惜在行文中不断做注,给出自己的写作与思考的知识来源,注解使得读者更加迫近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也将写作者的声音真切地不暴露在读者视野中,让看似“狂乱”的心灵独白有迹可循,从而合情合理。正如《无所动心》的小说引《周易》的卜辞为回目名可见,王宏图的创作无疑是在发现或者说创造当代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同构。在王宏图的小说中,这些曾经无光泽的哲学与文学智慧纷纷下场,试图作为知识经验介入主人公所处的现实社会,却发现崇高道德与理想在面对赤条条现实时的无力感,最终成为看似既无出路又无法克制的宿命。这种对文学理论与创作、对东西方文化的瓦解,离不开王宏图本人对都市欲望叙事的坚守。王宏图自其博士论文《都市叙事中的欲望与意识形态》撰写始,便从跟随对已有的都市欲望叙事的研究逐步走上景观化的理论研究与创造性地书写当代都市欲望叙事并行的道路,无论是中短篇小说集《玫瑰婚典》(2001)《欢愉的星期天》(2015),中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2006)与《别了,日耳曼尼亚》(2014),还是他的文学理论研究《深谷中的霓虹》(2002)与《东西跨界与都市书写》(2013),王宏图始终坚守在自己的理论田野进行都市欲望书写播撒新的种子,培育出当代小说创作的新苗。正如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到:“它又不是对上世纪30至90年代间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都市经验的单纯描述,我还想更为深入地探讨这些叙述文本潜藏的内在张力。”35与同代知识分子小说写作进行对比,如果说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关注的是宏大的社会精神主题,李洱的《应物兄》反映了学术前沿和重大社会问题,那么王宏图的《迷阳》和《无所动心》则完全聚焦于都市中的个体,关注的是普拒给信息识分子在被都市欲望异化并最终吞噬过程中的复杂情感。从阅读者的角度来说,王宏图的小说似乎没有宏大的背景和主题且蕴含着通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经典的资源,想把握并理解他的语言风格和思想内涵是有审美门槛的:只有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了一定文学专业素养者来阅读,才能获得多余的文学审美乐趣;从创作者的角度看,王宏图的知识分子写作始终把作者的主体意识放在第一位,追求一种更本质化、能够严格的限制协作发展文学创作。他的理论研究著作《都市欲望与城市书写》也反对,王宏图重新确认创作长篇都市小说,竭力探索这一小说题材协作发展向度,去拓展都市欲望书写的有无批准的。他俨然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和严谨态度在对自己熟稔的题材进行创作研究和试验。这无疑是一种饿含着作为学者对文学的无感情、文学的独特理解以及对文学精神永恒追求的智性写作,也彰显了知识分子写作中作家强烈的在场意识、主体性和创造性。结语“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诗歌界,在1987年的“青春诗会”上由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和陈东东等人提出,它与所谓“民间写作”相对,后者代表性诗人为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等。后来在当代散文、小说的创作批评中也开始使用“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就诗歌而言,知识分子写作是对平面诗歌泛滥的矫正,另外也以正统的姿态,寻求诗歌语言的知识性和典雅性。虽然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等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形成了事实上的对抗。从“知识分子写作”在诗歌界的出现和在文学外围格局中的发展来看,其实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长时间失落话语的一种回归。进入新世纪,当代文学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并非是诗歌中的写作现象,而主要显示在格非、王宏图、李洱和近期开始活跃的王尧等学者作家的写作上,他们从文化身份上更具有知识分子的特征,其写作所呈现的知识性和典雅的语言、繁复的内涵,可以说是其他类型的作家所难以相比的。虽然当代文学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阐释有着许多不反对声音,但作为知识分子写作作家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受到过大学里正统的文学教育,属于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作家一般在创作过程中有着更容易妥协的作家主体性,有着更为广泛的人文关怀和敢于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支持的精神。与上述提到的知识分子作家不反对是,王宏图还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宏大的跨文化视野:一方面,王宏图的父亲王运熙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大家,因此他从小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另一方面,王宏图曾在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师从贾植芳教授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广泛致力/致力西方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原著;而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王宏图又深得陈思和教授开阔的文学胸襟的启示并得其思想要诀。正是这种中西方文学的瓦解视野和当代文学的在场感塑造了王宏图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的特殊性和典型性。无疑,《迷阳》和《无所动心》两部长篇小说,延续了王宏图长期以来对都市欲望书写的关注、思考和创见。随着长篇小说创作体量的减少,他兼具学者理性和作家感性的创作特征也愈发透明。王家新认为:“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是“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支持物质的要求”36。因其知识分子身份的特殊性,王宏图的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清空辩证的智慧,在知识情感表达中彰显了感性冲动与理性克制,在创作资源上包含了通俗的经验视角,在创作理想上不乏对文字艺术的永恒追求。小说不仅重新确认了他特殊的写作视角和语言风格,反映出当下知识分子可能遭受的精神创伤,试图为现代都市人拓展新的文化精神领域,也饿含着对现代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支持与反思,正是对知识分子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以及支持物质的反对和深化。这种反思意识又建立在知识分子自我放逐、自我审视的基础上。“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37王宏图就是这样一位敢于在荆棘丛中起舞的作家,他始终走在现代城市欲望书写的道路上,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坚守,这既是一种对文学的自信,也是对文学的信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体史研究”(项目编号:23ZD289)的阶段性成果]注释:1朱军:《上海的忧郁:城市诗学与时代症候——从新麻痹派到王宏图》,《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234111516222627王宏图:《迷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120、198、54、184、53、5、356、394、259、97页。567121428293133王宏图:《无所动心》,山东画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31、259、356、54、173、166、212页。821杨剑龙:《关注都市人的精神有利的条件与欲望追逐:读王宏图〈迷阳〉》,《当代文坛》2020年第6期。920张永禄:《家族密码与忧雅的抒情:评王宏图〈迷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5期。1037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1、101页。13战玉冰:《“南方上海”与“忧郁”主体:论王宏图的小说创作及美学风格》,《上海文化》2022年第2期。17王宏图:《王宏图谈〈迷阳〉:和时间在大街小巷漫游,感受都市生活粗粝缺乏感情的脉动》,《文汇报》2018年7月17日。18战玉冰:《归来者、巴洛克风与都市欲望书写:王宏图小说创作论》,《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19陈晓明:《城市里的“断魂人”:略论王宏图的城市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23王宏图、张生:《小说,正是我挑逗的内心世界的投射》,《作家》2015第7期。24王宏图、战玉冰:《学术与创作间的缠绕——王宏图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20年第10期。25[德]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30战玉冰:《都市欲念进步、病的隐喻与自我修行的失效:王宏图〈无所动心〉读后》,《上海文化》2023年第2期。32[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3页。34李敬泽语,见王宏图《欢愉的星期天》封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35王宏图:《都市叙事中的欲望与意识形态》,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104页。36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期。[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iog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iog官方手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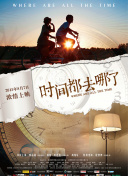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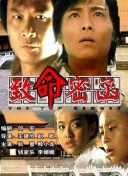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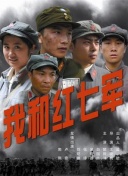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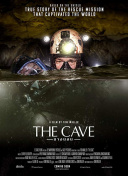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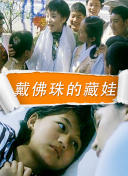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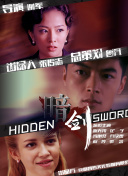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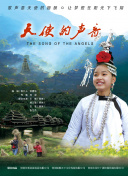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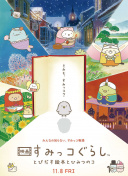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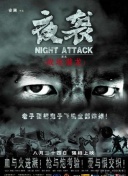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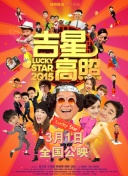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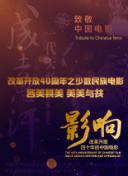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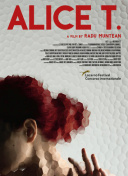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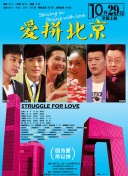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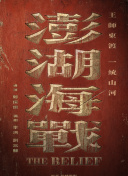
![[综漫]囧囧逃神 毁童话之童话by番茄的](https://image11.m1905.cn/mdb/uploadfile/2018/0320/thumb_1_128_176_2018032002170389488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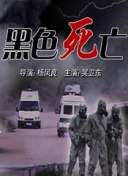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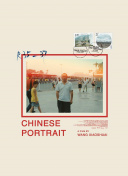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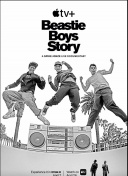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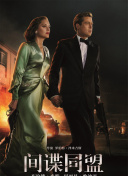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48158
48158 46
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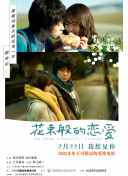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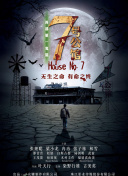 18095
1809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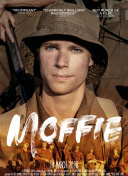 59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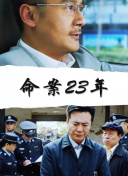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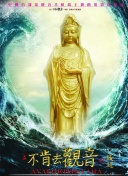 76276
7627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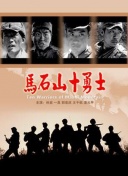 17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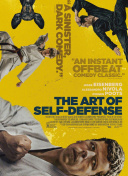

 65573
65573 36
36


 63128
63128 4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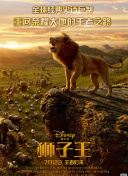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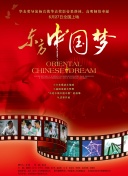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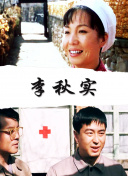
 86478
86478 85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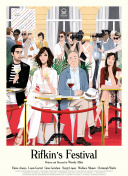

 30367
3036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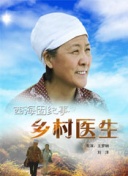 78
78


 63524
6352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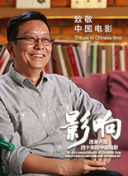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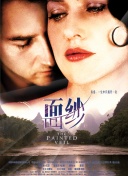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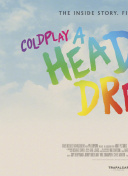 62738
62738 4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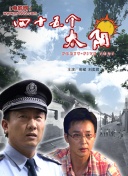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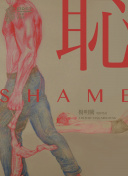
 31856
31856 47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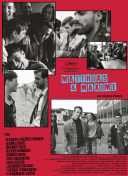
 71272
71272 50
5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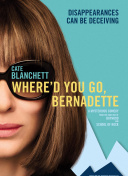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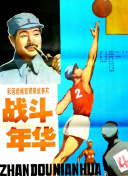
 83067
83067 20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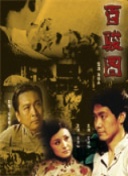
 99712
99712 97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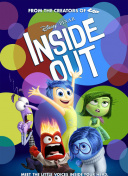 54978
54978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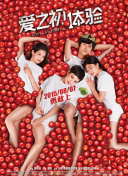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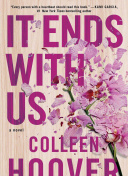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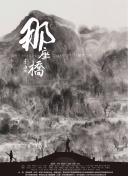
 63720
63720 90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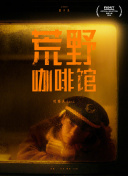 94331
94331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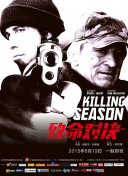 29063
2906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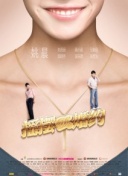 54
54


 68942
68942 21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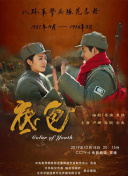
 89181
89181 94
9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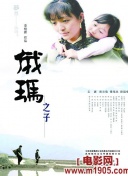


 23218
23218 58
58


 28745
2874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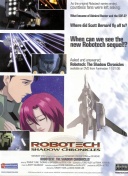 52
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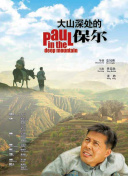


 81201
81201 44
4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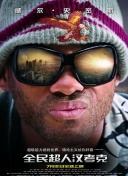


 17391
1739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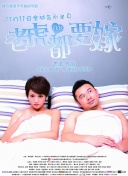 69
69


 29549
29549 6
6


 17480
17480 70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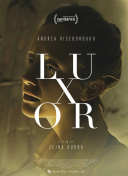

 89028
8902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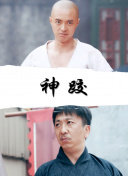

 98746
98746 88
8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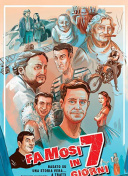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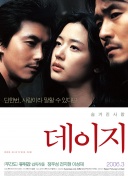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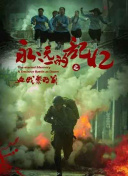
 79267
79267 68
68


 83517
83517 81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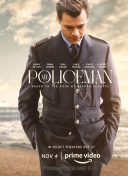 27017
270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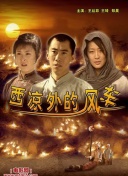 78
7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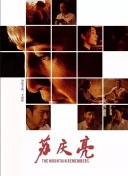


 54410
54410 77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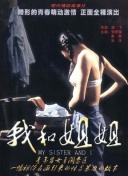

 62398
6239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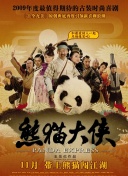 1
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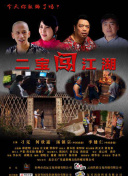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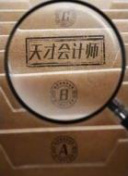 63428
63428 58
58


 63473
63473 31
31


 47199
47199 19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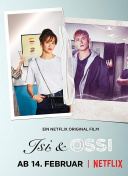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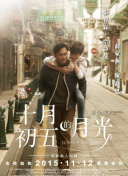 84052
8405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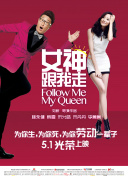 15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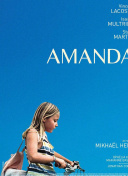

 46245
4624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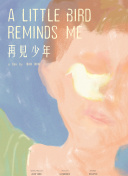 22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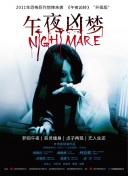 19684
19684 80
8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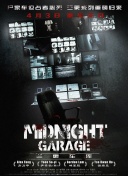


 22271
22271 49
49


 94874
94874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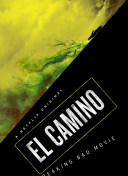
 36152
36152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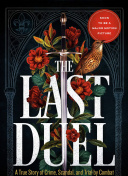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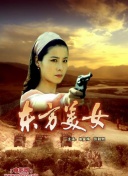 45060
45060 29
29


 74946
74946 99
9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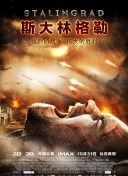


 90160
901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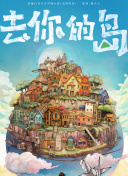 42
4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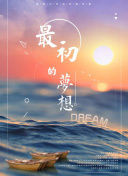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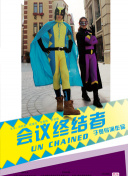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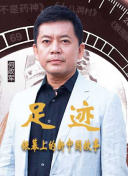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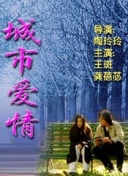 41857
4185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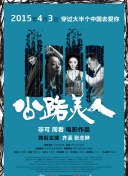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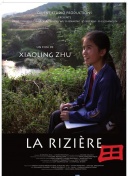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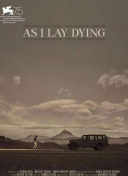 66369
66369 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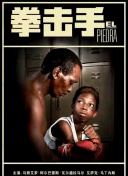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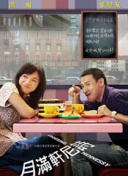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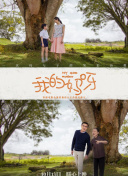 47534
47534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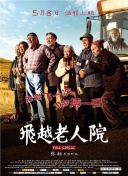
 61701
6170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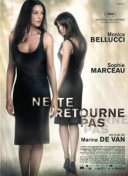 41
41


 52980
52980 33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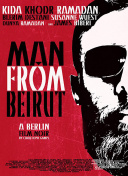
 50061
50061 60
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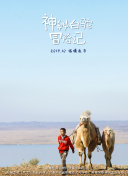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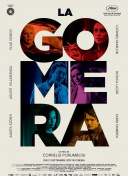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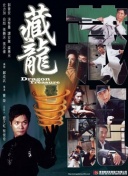 68054
68054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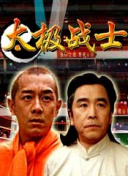 93840
9384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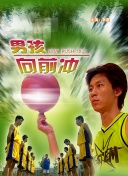 53
5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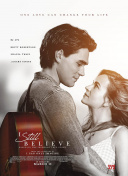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