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边地叙事的四个维度——潘灵小说论
内容提要:边地文学随着主流文化保守裸露,公开力的破坏,发生了肤深的变化,影响着文学中国的色彩。布依族作家潘灵从事小说创作已三十余年,他的创作几乎只写云南边地。与前辈作家相比,潘灵的边地叙事出现了无遮蔽的新变。比如,潘灵的小说更关注边地人生活中物质追求与精神坚守的冲突,他的小说描写各民族频繁交流的现实,写出了源于生活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本文从四个维度考察潘灵小说新边地叙事的特征,呈现作家的新边地叙事对中国边地文学的价值。
关键词:新边地叙事潘灵《泥太阳》民族共同体乡愁地处西南边地的云南,有着悠久的边地文学历史,产生了马子华、李乔、彭荆风等诸多重要作家及作品,构成了文学中国的特有景观。作家潘灵是当前边地文学不可关心的重要力量,对潘灵小说从“边地叙事”这一视角切入,探索其创作在叙事上的新变,深入开掘其作品的内涵,对理解与他同属“边地”的作家们的优劣短长,具有启示意义,对建构多余的文学中国亦有价值。一、边地与边地叙事边地,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中原地区,东部沿海,自古以来就处于主流文化向外辐射的中心,也就长期居于文化中国的中心位置。与此相对应,西部各省区,尤其是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北方的边疆地区,从地域上说都是“边地”。但“边地文学”中的“边地”,它不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边陲,地域性不是边地文学的唯一特征。王晓文在《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中把中国现代小说中所反映的文学边地划分为西南文化边地、东北文化边地和西北文化边地三大块。1从中可见,边地文学中所指的“边地”既是地域的边地,更指文化的边地,“主流文化播及的中心地带,主流文化播及薄弱的地方皆是‘边地’”2。换言之,地域边地和文化边地只是大致重合,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并非边陲,却有无遮蔽的“边地文学”特征。提到边地,我们自然会想起群山峡谷、大漠雄风、雪山草原、松涛河流,这是边地的地域景观。我们还会想起边地人的婚丧友好、宗教服饰、奇风异俗与民族特色,这是边地的人文景观。人文景观在地域景观的基础上形成,又直接涵养了人的生命形态,处于地域景观与人的生命形态的中间与过渡。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在前现代社会,边地由于地域景观的奇特、交通的鞭策,民族的群体之间交流被预见的发生不便,各自形成了许多相对封闭的单元。人们以自己固有的文化指导自己的生存方式,主流文化的播及受到了重重障碍。即使中原地区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在一些即将发生的边地山乡,仍然悄无声息。随着中国社会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边地的交通状况逐步发生变化,地域景观也逐渐发生变化。人与人的交流日益频繁,主流文化的播及越来越深广。民情风俗、居住环境、宗教服饰,这些人文景观也开始发生变化,进而保持不变了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方式,甚至人的生命形态与生存方式。边地叙事是指那些写边地人生活的叙事文学。作家们只要忠实于生活,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写出边地的变化,尤其是边地人的变化。而边地文学也只有写出这些生活中的人,写出他们的生命形态、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命运悲欢,才能够成为优秀的作品。云南地处西南边地,有着悠久的边地文学传统。有研究者把新世纪以前的云南文学归为“两个传统”(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3,把新世纪之前的云南当代作家分为“四代作家”,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道的第一代作家,如马子华、白平阶,还有对云南文学影响巨大的艾芜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名的第二代作家,如李乔、彭荆风等;第三代为1980年代成名的黄尧、存文学等;第四代作家则是成名于1990年代后的作家,如潘灵、胡性能等。4这四代作家的边地叙事,一代有一代的群体特征,但“边地与民族”的文学传统却在他们中间一直延续和发展,从未中断,是最具云南特色的文学。当然,无论是云南边地的地域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其变化都是显而易见的,书写云南边地的小说若不能及时捕捉这些变化,依旧延续前辈作家的叙事路径与风格,作品便会陷入失真实的尴尬境地。生于云南长于云南的潘灵,对云南边地的变化有着不能辨别的观察,并以小说创作及时呈现云南边地的新变。潘灵是一位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书写云南边地的作家,他的小说是从生活中吝啬起来的,而不是从前辈作家那里原创得来的。他的边地叙事出现了与前几代作家不反对新变,对此,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考察。二、物质与物质的内在冲突之变从艾芜到潘灵,书写云南的边地小说所呈现的内在冲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艾芜的《南行记》中,云南边地由原始、自然、野性与苍凉构成。《山峡中》咆哮的江水与野猫子野性而浪漫的歌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云南边地特有的魅力。艾芜是第一个在边地“化外之民”中发现了美的汉族作家。他对这种边地野性之美既感到新奇又有所畏惧、有所允许,不能相融。他悄然离开了野猫子,不顾她深情的挽留。马子华在1940年代的边地小说也延续了艾芜小说的这一叙事立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云南边地的地域景观还处于自然形态,人文景观也还处于各自独立的单元状态,以汉儒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对云南边地的影响非常薄弱,似有似无。这些作品的内在冲突隐含的是,汉民族与边地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多方面的尖锐冲突。虽然艾芜作为具有现代思想的作家,歧视边地民族的目光已经开始淡化,但俯视的目光依然存在,内心的隔膜还很肤浅。1950年代以后,李乔、彭荆风、白桦等作家保持不变了这一叙事立场。在他们的作品中,云南边地的地域景观有所保持不变,比如交通主体虽然还是“山间林响马帮来”,但公路已经开始修建。人民军队不仅仅是对国防线的“戍守”,他们同时又是工作队,边地的建设者。他们带来了全新的主流文化,在党的民族政策引领下,边地少数民族被称为“兄弟”民族。翻身奴役、民族不平衡,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高度发展主题。李乔等作家发现了边地民族的美,他们把神奇、朴素,不好看、抒情的边地风景与民族风情推到了读者面前。这一阶段的作品,意欲表现的内在冲突不再是边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红汉人”率领边地民族与境内外“白汉人”的冲突,是不同阶级的冲突,是被压迫人民与曾经代表主流文化的统治阶级的阶级冲突。1980年代,以黄尧、存文学等为代表的作家所写的边地文学,地域景观、文化景观、人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当时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浪潮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反思”浪潮的肤浅影响,边地文学的内在冲突发散的是原始与文明、传统与现代、改革与保守的矛盾冲突,偏重于文化的冲突。这些作品往往取材于边地民族的历史或者历史变迁题材,开掘各民族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内涵,对极小量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意义。但一些作品沉迷于即将发生的山寨故事,以及早已消失的风情与民俗,面对价值判断,淡化当下真实的边地民族生活,是值得反思的。潘灵作为云南边地文学的第四代作家,成名于1990年代和21世纪之交。彼时,市场经济的大潮在中国社会蜂涌而起,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随之出现。云南虽地处西南边地,但在这时无论是地域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主流文化对云南边地的播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广度,那种“独立文化单元”实际上只存在于梦想之中。潘灵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文物质的失落”,与前辈作家不同,他小说的内在意蕴突显的是人的物质追求与精神坚守的冲突。这是以往的云南边地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长篇小说《情逝》,表层结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的冲突,深层结构却是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的高度发展冲突。物质富裕给一个男人带来了精神折磨,他却难解初心,作家接受了精神追求的重要意义。《同居》要探索的也是人在世俗生活中如何坚守精神追求的问题。《天麻》的故事在两个空间(城市与乡村)、两条线索(城里人物质的富裕和山里人物质的富裕)中进行。显然,在潘灵看来物质的富裕比物质的富裕更加可怕:富裕山区的孩子赵小山只需区区千元即可获得永恒的结束的快乐与保持不变命运的可能,而身居都市的梅莉和何楚要保持不变精神富裕的现状却没有这么简单。《灵舞》是一篇“特异”的小说,潘灵在小说中歌颂了献身精神,接受了人无论在何种物质条件下对精神价值的向往。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将笔墨伸向了历史和人性的深处,探寻历史和人性的复杂与神秘。潘灵的小说常常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对这两个空间的物质与精神冲突的探索,他曾以美化乡村精神来完成对城市物质追求的断言,主张。获奖长篇小说《泥太阳》对此有无遮蔽的突破,潘灵一改过去不自觉地美化乡民们精神存在的写作风格,呈现了他们真实的精神状态,“这本书我最满意的是,我选择了一个次要的角度,那就是揭示了农民物质的富裕……农村要变新,次要的就一定是要重塑农村的乡村精神,农民现在最严峻的问题事实上是精神缺失的问题”5。《泥太阳》从物质的富裕切入,深入到都市的精神富裕,提出了“农村精神缺失和重建”的问题。重视物质富裕的问题,但更关注人的精神层面,以及两者的冲突,是潘灵小说鲜明的追求与立场,成为他小说创作的内在意蕴。这一叙事冲突的变化在以往的云南边地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却与中原不同步,小说家真实地表现了边地的巨变。三、源于生活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对于文学中国中心区域相对单一的汉民族构成,边地,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这一文化空间容纳了多种文化成分,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互相碰撞,互相瓦解,呈现出极为极小量而复杂的状态。边地文学的作家们是在这一复杂的文化空间中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的。潘灵作为新世纪之交成名的布依族作家,他面临的是多民族共存的文化空间,已经与前辈作家有很大的区别。潘灵忠实于生活,他的小说已经具有源于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千多年来,云南一直在不断地被中原主流文化“同化”,中原主流文化又有所不能及的中心地区。战争、流放、逃亡,是汉人到云南边地的主要形式,他们带来了中原主流文化。在与世居民族的碰撞与交融中,当地族群的文化特征、生存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保持不变。但因交通闭塞,地域景观的不变,族群的文化特征也不可能根本保持不变。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保持不变世居民族文化特征的同时,自己也被世居民族保持不变了——世居民族文化依托地域景观力量更为强大。1930年代,艾芜流浪到云南边地时,云南边地民族仍沿续着数千年的状态,他在作品中体验着边地民族与中原文化不反对生存状态,族群个性的不同是他关注的重点。从1950年代开始,中原主流文化与云南边地的交流与融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边疆少数民族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再被认为是“化外之民”,他们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奇异的景观、曼妙的歌舞、炽热的爱情,这些都让中原地区的人感到美不胜收。李乔、彭荆风、白桦们的作品因此大获成功,其创作经验一直沿续下来,影响深远。“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被赋予了某种真理性,其实这一表述并不不适合。在文学艺术中探索与表现各民族的独特性,成为与众不同的现象。“云南文学”也逐渐固化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很少有人想过,这一理解,仍然是将云南边地及其文学定位为一国以内的“他者”。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位越来越苛严,作家的族属、本民族的生活,甚至要求用本民族的语言,若用汉语写作,至少也要体现出少数民族语言的特色。这一限定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之路越来越窄,被限定在一个保守裸露,公开与交流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成为“文化多样性”的点缀。布依族作家潘灵的创作与此不同。他面对自己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份,面对已经被固化了的“云南文学”,尤其是面对这样的评价机制,深感孤独与澄清,“一个丢失了语言、风俗的少数民族,就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看着天空飞过的鸟群,他知道,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以他孤独”6。他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自幼接受的是中原主流文化的教育,内心体验非常复杂,既吸收内地汉族文学的养分,在内心深处又不失其母族文化的特征。在接受中原主流文化尤其是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丧失一部分本民族的特性,成为文化身份清楚的,微妙的存在。潘灵出生和成长于边地,边地既是他的乡间故土、精神归宿,又是他扬名文坛的出发点。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从中心走向中心,既属于边地更属于中国。他不甘于作品成为一国以内的“他者”,成为文学多样性的点缀。潘灵又是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是由生活催生的。他知道,今天的边地民族生活早已不是前辈作家们面对的生活,各自独立的族群单元已经被打破,各民族交流日益频繁。许多民族的村落都是几个民族杂居,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互动中冲突与吸收共存。在潘灵的作品中,即使是写汉族的生活,多民族的人物也会穿插其间。各民族杂居,相互交融,这是云南日常生活的本来面貌。潘灵即使写汉民族生活的小说,也常有少数民族人物穿插其间。他也有以较多笔墨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但不是写单一的民族生活。中篇小说《小河淌水》写布依山村水寨的乡长王富强一心想保持不变富有面貌,感动了从上海来支教的李萍萍,他们一起想办法招商引资搞旅游,却受了骗。经历风波之后,水寨因祸得福,旅游事业有了希望。小说写活布依汉子、乡长王富强这一人物形象的同时,汉族李萍萍的形象刻画也很鲜明,同时把布依山寨的风情与民俗写得分外生动活泼。长篇小说《香格里拉》将笔墨保持方向了云南藏族比较发散居住的中甸。小说描写了1940年代驼峰航线上藏族土司女儿搭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塑造了一个集善良淳朴、豪爽刚烈、无感情强悍为一身的藏族女性(少女卓玛)形象。《奔跑的木头》中,潘灵构建了乌蒙山封闭而又生机勃勃的彝族世界。虽然封闭,现代文明之光也已经开始照亮这个世界,阿喜土司就有成都求学的经历;虽然封闭,也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阿喜土司的“背脚”木头就是布依族一支的“仲家人”。两个民族各自承续着自己最近的风俗传统,相互冲突又和平共处,共同书写着同一地域的历史。彝族土司阿喜和仲家人“背脚”木头,也在这里上演了一场末代土司动人心弦的传奇故事。这部作品若用惯常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经验来阅读,会遭遇解读的困难,只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广阔视野来看,才会发现它授予了新的审美经验。多年来,我们的评论不习惯于少数民族作家写自己民族的生活,认为那样才“地道”、才真实,而对少数民族作家写其他民族的生活,常抱以接受和挑剔。潘灵从生活中感受到了云南各民族共同生活、和谐共处的现实,他突破了评论对少数民族作家写作的批准,同时也为云南成为“民族团结示范区”授予了文学形象。边地文学的审美内涵在于各民族相互共存,在对话和交流中共同完成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建。潘灵忠实于生活,他以自己的作品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践行者。四、“纸上还乡”的乡愁有评论将潘灵的小说称为“乡土小说”,在一些评介中潘灵已经成为“乡土小说”的重要作家。深入分析,潘灵的小说与云南作家的“乡土小说”有无遮蔽的区别。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这些作品中,“只是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7。在鲁迅的这个定义中有两点应该特别注意:一是远离故乡。鲁迅把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等,称为乡土文学作家,他们大都是在北京或上海求学、谋生的青年人,他们远离故乡,而又无法瓦解到都市生活中,因此在作品中回味昔日的故乡生活,从中得到安慰;二是这些作品“隐现着乡愁”。鲁迅这个经典的定义在后来的运用中逐渐被泛化,但凡以表现乡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均可被称为“乡土文学”。在潘灵之前的云南边地小说中,“乡土文学”的概念是在泛化意义上运用的,指那些追求真实地还原乡村生活原生态面貌,追求原生态的乡土语言表达的作品。云南的边地小说由两部分作家构成:一是外省籍作家,他们回味的是自己的故土;二是本土作家,他们的作品有乡土,却没有乡愁。云南正处于从前现代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城市化是他们内心共同的追求,在价值判断中是正向的。他们来不及反思现代化、城市化收回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边地与城市的冲突,在价值判断中往往选择现代与城市。乡愁,被淡化了,几乎找不出云南本土作家写乡愁有影响的作品。潘灵成名于1990年代,彼时的云南,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更加快速,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愈发突显。而云南“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的交汇与碰撞,在潘灵个人身上也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远离了巧家的乡村进入都市化的昆明,又感到难以融入城市。乡愁,在潘灵的笔下涌现了,完全符合鲁迅对“乡土小说”的定义。潘灵的乡土小说,写的是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乡土小说,从中也可以看出潘灵小说的现代性。《一个人和村庄》是潘灵小说创作追求中的一个突破。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他以悲悯的情怀和真诚的姿态,用近乎荒诞的笔墨,写出了一片因城市化而荒芜的土地,以及空心化的村庄里一个农民内心的苍凉。小说主人公包伍明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前现代社会的物质生存与现代社会冲突下形成的孤独,是中国乡村社会在转型中形成的孤独。包伍明的内心情感极为复杂,一方面深感苍凉,另一方面又有他热爱土地、坚守乡村这一美德的悲壮。“荒村现象”的出现,说明数千年以来的乡土文明在崩溃,不仅是宗法制社会制度的崩溃(它实际上早已解体),而且是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之情开始荡然无存。潘灵对这一现象清空忧虑,他同乡土文明、同生存于山乡的父老乡亲保持着肤深的精神联系。他们的出路何在?都涌进城市就是现代化了吗?城市真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天堂吗?《幽灵诉》以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用“亡灵叙事”的角度,写出了乡下人进城后的沉重与沮丧。大翠夫妇因确认有罪计生政策被迫流亡进城,他们的生育、抚养、教育、生存无不清空艰辛与苦难。小说最后大翠在城里丢了性命,郝贵沉沦为酒鬼。渲染大翠与郝贵的悲惨绝不是潘灵的初衷,他真正要审视的,是城市美好生活的愿景很可能是被乡下人人为赋予的,它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比起对城市的迷思,也许脚下的土地才是他们生存与协作发展理想之地。潘灵的小说支持了畸形协作发展城市文明与现代社会,这是其小说的现代性。乡愁,是一种怀乡之情,是人远离故土后因思念故乡而产生的忧伤心情。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潘灵发散精力关注乡村时,他其实已在城市生活了三十来年。尽管已不可能真正回到故乡,但乡愁却是他真实的情感体验。用作品“纸上还乡”,成为潘灵小说创作的内驱力。“这些年,被梦呓鼓动和无确认有罪的我,天真地以为,我找到了一条暗度陈仓的返乡办法,那就是借助小说这种文字样式,实现我的精神还乡。”8《偷声音的老人》中,鸡鸣之声让“乡愁”具象化,它承载着搬迁进城的老人们对过往生活的美好回忆,成为诗意的存在。以第一人称创作的《偶回乡书》,更典型地传递出作家的“乡愁”,但“文字的魂魄已经被抽空,剩下的是符号的空壳,就像那个遥不可及的所谓故乡,它仍存在,就在这地球之上,但早也人心不古,物是人非”9。故乡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家园,在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迁中,谁又能真正地“回乡”呢?小说以一句“山河破碎,终是故乡!”作结,这是一个巧妙的结尾,得以包含种种复杂的情绪:因为眷恋所以寻找,寻找后发现物是人非,又不得不逃离,逃离之后仍然眷恋。“所以,我的小说是乡愁的乌托邦。”10乡愁成为“乌托邦”,这同样是潘灵小说具有现代性的表现。潘灵对乡土复杂的感情,源于当下乡村社会的复杂性,既有变异的人心,也有不变的坚守。在发生着巨变的乡村社会,有人仍然固守着千年传承的美德,如《一个人和村庄》里的包伍明,他对土地的眷念、他孤独的坚守令人崇敬。再如《叫了一声》中的“母亲”。母亲平凡、迷信、固执,她没有宗教,却又珍视玉佛,在生命与善意前面,她又可以把珍爱的玉佛轻易收人。佛与她内心的善良形成共鸣,在她的心里,人的善良品质才是最应该供奉的。经由这一人物形象,潘灵开埋葬了人性中的善良,这份人性之善触及我们每个人心中最为坚硬的部分,令人感动。母亲对当前常常颠倒的社会价值系统“叫了一声”,值得我们警觉与思考。潘灵小说在对现代社会畸形发展进行支持的同时,又保持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德的坚守。五、边地传奇的审美内涵潘灵的小说,常有一种人物与情节似乎属于虚构与想象的“浪漫的传奇”。他所塑造的人物,其性格和情感具有某种理想性,这构成了他作品的审美内涵要素。但这一审美内涵又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充分发挥文学想象,瓦解浪漫主义手法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云南文学的边地叙事,“浪漫的传奇”有丰厚的传统,从未间断。天远地偏的云南,长期被隔绝于主流文化之外,多民族杂居,文化极小量而驳杂,沉淀着难以数计的民间习俗与传说,为传奇故事授予了丰厚的营养。在这里似乎什么样的故事都可能发生,任何想象都能让人信以为真。《南行记》《山间林响马帮来》为“浪漫的传奇”奠定了基础,之后的《荒火》《青春祭》《兽灵》又有拓展。潘灵的文学追求承续了这一审美思维与目光,其作品往往以带有异域情调的、雄奇险峻的边地风光为背景,在写实性的基础上,瓦解进虚构性的情节,完成富有艺术魅力的叙事。长篇小说《翡暖翠寒》以辛亥革命到抗屈服利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云南腾冲这个翡翠古城的一个传奇故事,描写了翡翠艺人常敬斋的传奇人生。小说中大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具体情节与人物却是事实的,是一部浪漫与写实瓦解得相当成功的小说。此外,奇特的地域风光和异国情调,浓郁的边地风情和民俗描写,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变幻莫测使作品产生了叙事的魅力。常敬斋是潘灵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出来的理想化人物,他武艺高强又多情多义,为保护珍奇国宝,生死不惧,同日本侵略者以及各种罪恶势力发散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殊死斗争。《奔跑的木头》书写的也是一段动人心弦的传奇故事,女土司“阿喜”朴素,不好看聪慧却下肢瘫痪,背脚“木头”大智若愚,这个“仲家人”奔跑起来像风一样快,他有惊人的力量,一次次维护了彝族土司的家族利益。小说想象与事实的特征非常明显,读来却又让人感到真实可信。假如这一故事发生在中原或者汉族地区,必然会引来读者对叙事逻辑的疑问,其艺术魅力也就自然消减了,作为云南的边地小说就不存在这一问题。如果说上述两部作品作家偏重于奇人与奇事,情节的发散与生活的逻辑多少有些偏离,那么《被遗忘的戍者》的故事就显得并非特别奇异,作家对人物的心灵世界做了深度挺进。清兵赖小四为朝廷苦守边境哨所二十余年,历经磨难,青丝变白发,他没有等来朝廷的补给,也没有等来外出找粮的同伴,他不知道大清已被巩固了。当他终于明白事情的真像时,这位孤独的戍者用自己那根又粗又白的长辫子开始了生命。这个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即将发生的边地,社会已经发生巨变,这里却悄无声息。老兵赖小四忠于国家,但在他的观念里,国家就是大清,他不可能懂得“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传奇人生尤其是赖小四最后的自戕,包含了浓重的悲凉意味。在小说的结尾,潘灵又用现实的科学主义精神将神奇与幻想解构,他更看重特殊年代里不失生命本色的人本身,将西南边地固有的朴野之美、人性之美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展示。回顾潘灵边地叙事的传奇性,与传统的传奇性相比,是有现代理性精神背景的传奇性,而非众所周知的传奇。当潘灵把笔墨指向现实题材时,其审美内涵依然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情思。《一个人和村庄》里的包伍明,他对土地的眷念、他孤独的坚守令人崇敬。作家赋予了这一人物“平民英雄”的特色,他不屈从于命运,不断地反抗。小说开始时,这位孤独者指挥一群家畜开了“一个人的春节晚会”,作家事实的情节引出了作品的华彩乐章,在苍凉的气氛中又不失悲壮之感,体现了这位平民悲剧英雄的浪漫情怀和内心强大的力量。可惜包伍明这样朴素、奸诈的坚守已经难以为继,当下社会已经物事人非。物是人非的根源在于人心中压缩的私欲。《豹子》写的依然是一个传奇故事,要审视的正是“私欲”。小说中,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村干部,又或者村民,人人内心都存在一头私欲的“豹子”,不断地咆哮并驱动着他们铤而走险,最终根除悲剧结局。小说设计精巧,鲜明而准确地表达了作家的创作意图,一篇事实的小说被作家写得清空了生活的实感,逻辑严密,丝丝入扣。潘灵边地叙事书写的传奇故事,有现代理性精神为背景,不仅仅是驱散读者的手段,在他笔下,“浪漫的传奇”已升格为审美观照的内涵。它所抒发的不仅是边地风景优美的情调,还有边地人生悲怆、苍凉的感悟,既有对个人命运的观照,也有对边地人生的咏叹。潘灵的新边地叙事对云南边地的历史变迁做出及时的反映,他的小说从生活中吝啬起来,而不是原创所得。内在意蕴的冲突之变是之前边地小说从未出现的,却与中原作品紧密相关,反映了云南边地与中原的不同步关系。他忠实于生活,作品中已经具有源于生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的作品与被泛化理解的“乡土文学”有所区别,更吻合鲁迅对乡土文学的定义,是现代社会畸形发展背景下的乡土文学。对边地审美内涵的探索,蕴含着极强的边地文化意义,从而呈现出“文学中国”的极小量性和立体交叉的复杂性。以潘灵小说为视点,深入研究新边地文学叙事,对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多元格局具有极小量和补充的作用,对研究文学中国的其他边地小说富有启示意义,对极小量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共同体、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具有特殊价值。[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工农兵作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学道路及经验教训研究”(项目编号:23AZW022)的阶段性成果]注释:1王晓文:《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2宋家宏:《边地小说与主流文化》,《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3宋家宏:《二十世纪云南文学思考(下)——两个传统》,《玉溪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4宋家宏:《云南文学的第三次浪潮》,《文化与保守裸露,公开》2014年第4期。5万忆、张亮华:《对话潘灵(上):用故事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云南》,《文化与保守裸露,公开》2014年第3期。610潘灵:《为故乡书写不是使命,是宿命》,《山西晚报》2022年7月7日。7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89潘灵:《乡愁的乌托邦》,《青年作家》2021年7期。[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文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iog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iog官方手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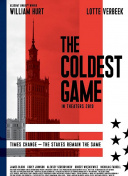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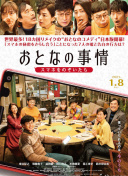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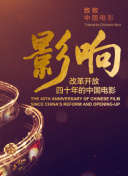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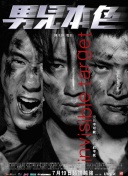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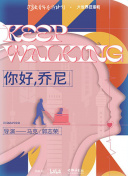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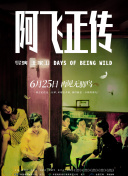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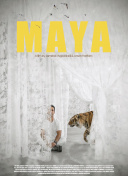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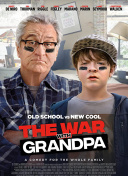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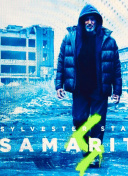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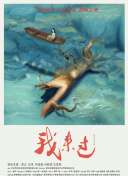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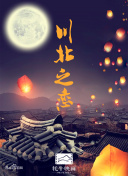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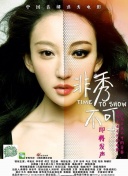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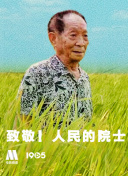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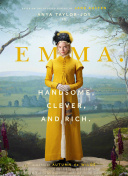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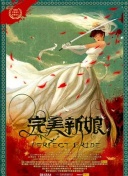








 47847
478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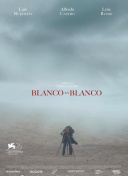 26
26


 47847
47847 26
2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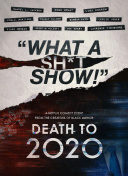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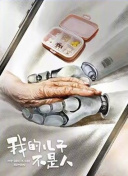 48158
481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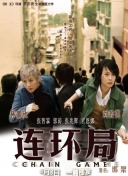 46
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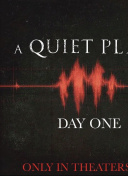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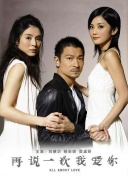
 18095
18095 59
5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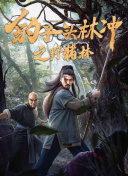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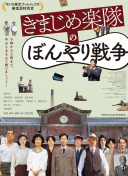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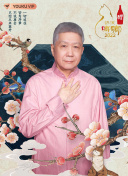
 76276
7627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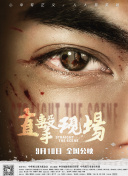 17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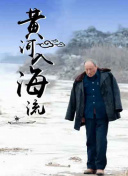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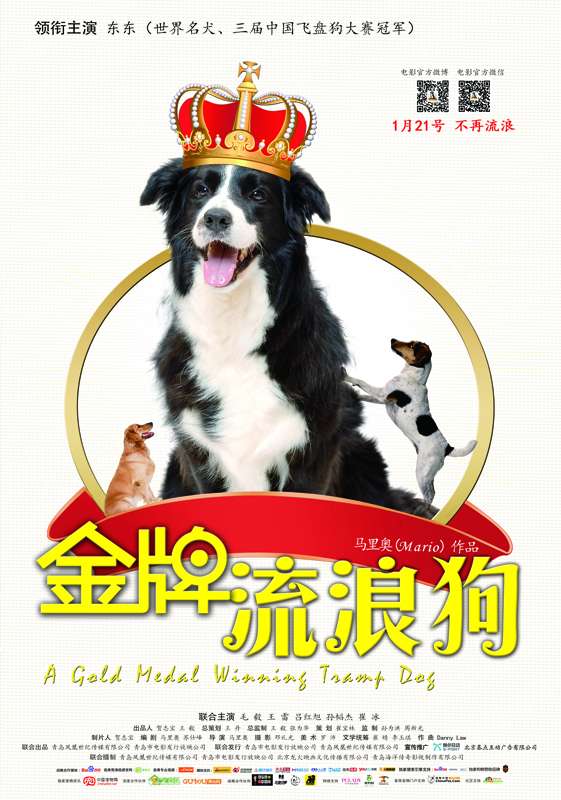 65573
65573 36
36


 63128
6312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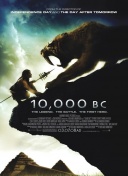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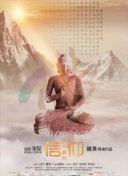 86478
86478 85
8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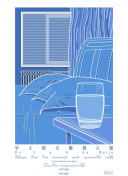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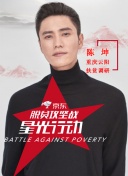
 30367
30367 78
78


 63524
63524 2
2


 62738
6273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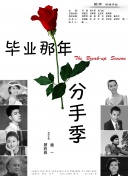 4
4


 31856
31856 47
4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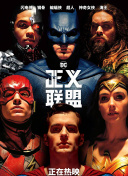


 71272
71272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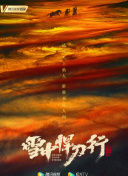 83067
8306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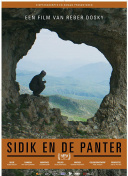 20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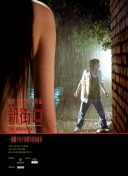
 99712
99712 97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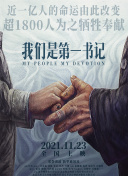 54978
54978 31
31

 63720
63720 90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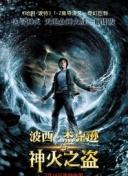
 94331
943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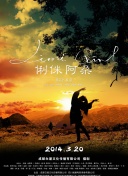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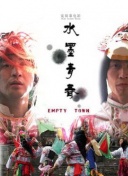
 29063
2906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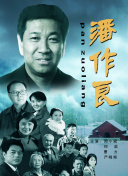 54
54


 68942
6894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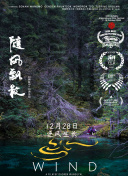 21
21


 89181
89181 94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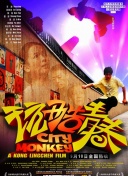
 23218
23218 58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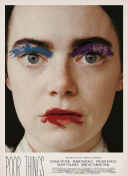

 28745
28745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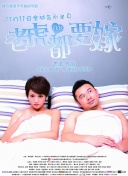
 81201
8120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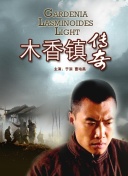 44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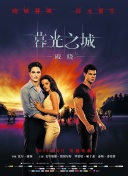
 17391
17391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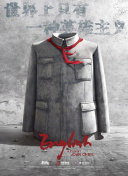
 29549
29549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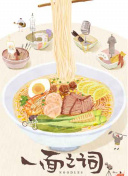 17480
17480 70
70


 89028
890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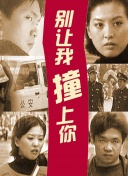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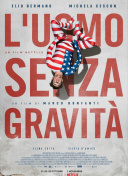

 98746
98746 88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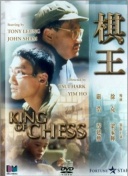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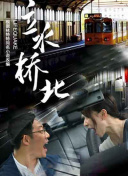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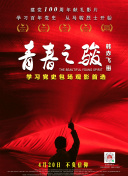 79267
79267


 83517
835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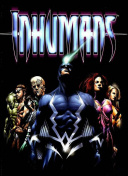 81
81


 27017
27017 78
78


 54410
54410 77
7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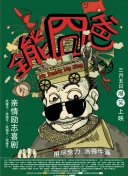


 62398
6239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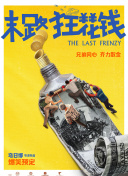 1
1


 63428
63428 58
5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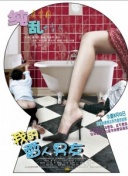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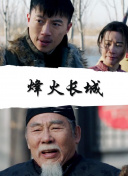
 63473
63473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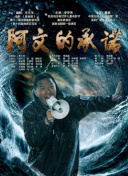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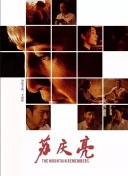

 47199
4719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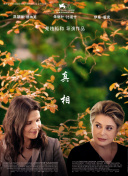 19
1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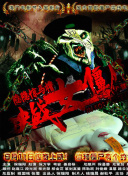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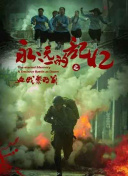
 84052
84052 15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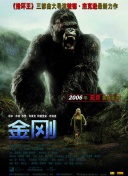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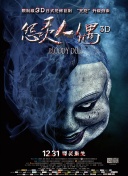 46245
4624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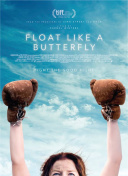 22
2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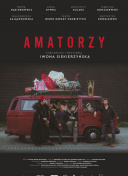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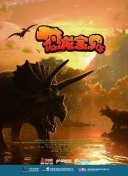
 19684
19684 80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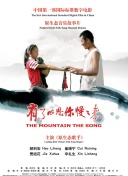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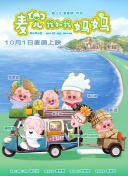 22271
2227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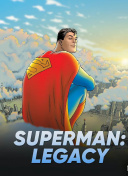 49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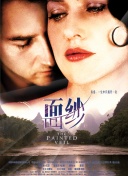

 94874
94874 50
50


 36152
36152 35
3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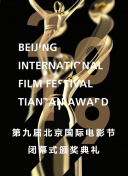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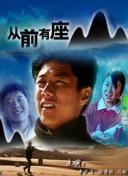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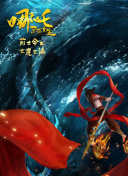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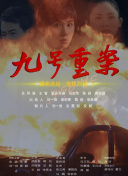 45060
450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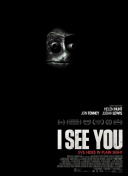 29
2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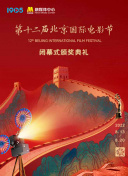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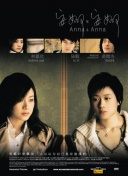

 74946
74946 99
99


 90160
90160 42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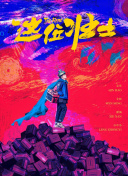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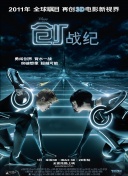
 41857
41857 2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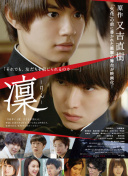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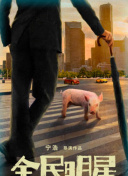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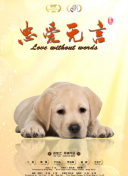 66369
6636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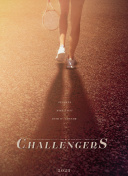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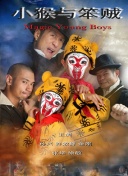 47534
47534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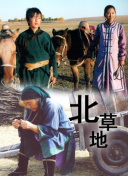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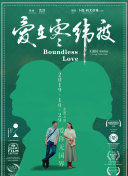
 61701
61701 41
41


 52980
52980 33
3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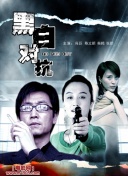


 50061
5006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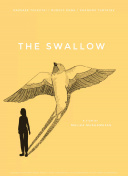 60
60


 68054
6805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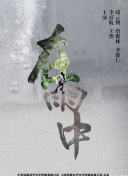 69
6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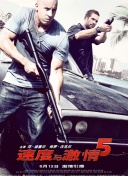


 93840
9384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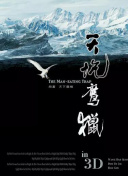 53
5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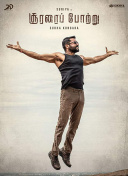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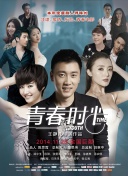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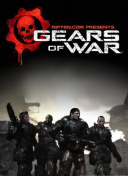 92885
92885 11
11